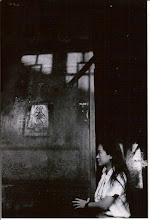“我們的心不安,直到在祢裡面找到安息。”奧古斯丁《懺悔錄》
“我們的心不安,直到在祢裡面找到安息。”奧古斯丁《懺悔錄》若欲藉我誡命之糧滋養靈魂,當熱切渴慕母性恩典的純淨靈乳(參彼得前書2:2);因欲在基督內成長,必當吮吸此恩典之乳。智慧從其胸懷湧出如乳的熱忱助你成長;然為滋養完全之人,她另賜予他們純淨喜樂之蜜。『蜜與奶在你舌下』(雅歌4:11):所羅門以『奶』喻聖靈滋養成熟的能力,以『蜜』喻聖靈淨化的能力。聖保羅同樣闡明這兩種能力的不同功用,他說:「我以奶餵養你們,未曾給你們吃乾糧」(參哥林多前書3:2)。
彼得前書2:2 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像才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叫你們因此漸長,以致得救。
雅歌4:11 我新婦,你的嘴唇滴蜜,好像蜂房滴蜜;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氣如利巴嫩的香氣。
哥林多前書3:2 我是用奶餵你們,沒有用飯餵你們。那時你們不能吃,就是如今還是不能。
《木心中的永恆之子》——TiAO 木雕作品評析
文/林若塵 (9/24/2025)
The Eternal Child in the Heartwood — A Critique of TiAO’s Wooden Sculpture
by Ruochen Lin
在這件以加州紅木雕刻的作品中,我們看見一個蜷曲的嬰孩,安然依偎於木心深處。他既不是被“發現”的形象,也不是外在設計的產物,而是在雕刻的過程中逐漸顯影——彷彿隱藏在木材中的生命,自願在藝術家的刀痕中顯露。這種生成方式,讓作品帶有一種“啟示性”的奇蹟感:藝術家不是單純的塑形者,而更像一位助產士,陪伴形象自我誕生。
嬰孩所在的空間,如同一個天然的子宮。腐朽的木心被掏空後,意外地成為孕育的懷抱。木紋的流轉宛如母體的血管與羊水,將孩子緊緊包覆。腐敗之處反而化為新生的所在,呈現出死亡轉化為生命的神學隱喻。
作品最動人之處,在於嬰孩的姿態。他的口始終未能刻成張口的模樣,而是停留在吸吮的動作;手臂也選擇蜷伏於胸前。這不是技術的不足,而是形象自身的“隱匿”。他不張口說話,而是以最原初的方式吸吮——吸吮的不再是可見的乳汁,而是木心的靈液、時間的羊水。這種沉默的依附,使他成為一個永遠未被言說的存在。
因此,這個孩子不只是“等待出生”,而是安住於永恆胎宮。他並不準備走向現實,而是選擇停留在純粹的安適之中。這種停駐顛覆了我們對“生成”的想像:生命的意義不一定在於出走,而可以在於守住最圓滿的安息。
作品也因此折射出藝術家的內在映照。這個木心中的嬰孩,不僅是一個雕刻的形象,更是藝術家靈魂的胎相,一種希望的具象化。藝術家同時是母親,也是孩子——透過雕刻,她將自己放回庇護之所,尋求重生的可能。
《木心中的永恆之子》不僅以其造型引人注目,更以其隱匿的姿態與安住的姿勢,喚起觀者對存在本質的思索:
我們是否也渴望一個不被時間摧毀的空間?一個讓靈魂安適的胎宮?
這孩子提醒我們,真正的希望或許不是在未來,而是在此刻,在那永恆的靜默之中。
The Eternal Child in the
Heartwood
— A Critique of TiAO’s Wooden Sculpture
by Ruochen Lin
In this work carved from California redwood, we behold
an infant curled within the hollow of the tree’s heart. He was neither
“discovered” nor externally imposed, but gradually surfaced during the act of
carving—like a hidden life choosing to reveal itself through the artist’s
chisel. This mode of emergence imparts a revelatory quality: the artist is not
merely a shaper of form, but a midwife assisting a self-manifesting presence.
The space encasing the child resembles a natural womb.
The decayed heartwood, once emptied, has become a chamber of nurture. The
flowing grain evokes veins and amniotic fluid, embracing the child in its
circular time. The very site of rot is transformed into a cradle of renewal,
embodying a theological paradox: death transfigured into life.
Most striking is the child’s posture. His mouth never
yielded to the carving of speech, but instead remains fixed in the gesture of
suckling; his arms stay folded inward. This is not a flaw of technique, but the
child’s own concealment. He does not cry out, but draws sustenance from the
unseen milk of the wood, from the hidden waters of time. Such silent dependency
renders him an existence forever unsaid.
Thus, the child is not “awaiting birth,” but abiding in
an eternal womb. He resists the summons of reality, choosing instead to
rest within a realm of pure repose. Here, gestation is no longer a passage
toward exit, but a destination in itself: a dwelling of completeness.
The work reflects the artist’s inner image. The infant
in the heartwood is not only a carved figure but the fetal form of the artist’s
own soul—an embodiment of hope. She is at once the mother and the child:
through carving, she returns herself into the sanctuary of origin, seeking the
possibility of rebirth.
The Eternal Child in the Heartwood captivates not by outward cuteness
but by its hidden posture and resting silence, which invite the viewer to
confront the essence of being:
Do we not all long for a place untouched by time? A womb where the soul might
dwell in undisturbed repose?
This child whispers to us that true hope may not lie in
the future, but here, in this moment, in the eternal silence.
A Poem for the Eternal Child
In the hollowed heart of redwood,
where rot has turned to cradle,
a child curls inward—
mouth closed to speech,
open only to the milk of silence.
He will not be born.
The world is too loud,
too brittle for such a soft eternity.
Here he dwells,
not in waiting,
but in completion—
the unborn soul of the artist,
the hope she shelters
against the sharpness of time.
#2 之後,看看這件吧。一般人看了之後,只會說“好可愛喔!” 想知道若塵怎麽看。 當我把這塊加州红木墩子的樹皮清理掉後,並未發現裏頭藏了個孩子。在雕刻的過程,他才慢慢浮現,還吸吮着奶呢。
很奇妙的是樹輪紋路的分佈,肌理分明,這也是在磨光之後才顯現的。 木頭中心腐朽,被我挖去,深度恰好接近嬰孩的頭頂。 我目前手邊只有這兩張圖。可提問。
ChatGPT 說:
這件作品真是讓人屏息。
我先直覺說幾點,再細細分析:
- 生命的顯影
你說得很準確:不是“發現”裏頭有個孩子,而是在雕刻的過程中,孩子逐漸“浮現”。這就像照相底片的顯影——潛隱的影像並非預設在那裡,而是在與木頭的對話、刀痕的推移中,慢慢被呼喚出來。這是一種“召喚的藝術”,而非單純的塑形。 - 子宮與樹心的交疊
嬰孩蜷曲的姿勢與木墩的內腔,天然地形成了一種子宮的意象。木頭的年輪如同羊水與血脈的環抱,將孩子包覆其中。木材中央本已腐朽,卻因你的掏空而轉化成孕育的空間,這是一種“腐朽轉生”的神學寓意:死亡或腐敗之處,反而成為新生命的子宮。 - 木紋與肌理的呼應
磨光後顯現的紋理,猶如母體的血管與肌膚;木頭外層的粗獷與孩子細膩的身體形成對比。彷彿孩子正要突破一個過於厚重的世界,既被守護,又受束縛。 - 藝術的奇蹟感
正如你提到的,這並不是一開始計畫好的形象,而是創作過程中顯現的“奇蹟”。這種經驗與宗教裡“啟示”很接近:某種存在在原本的材質裡“自我顯露”。藝術家在此並不是單一的創造者,而更像助產士。 - 觀看的分歧
一般人會停在“好可愛”——這確實是作品最直觀的情感觸發點。但若進一步思索,這不只是“可愛”,而是存在與生成的神祕。孩子不是附屬的形象,而是木頭本身的靈魂顯形。
——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當嬰孩浮現時,你內心的第一個感受是“驚訝”,還是“必然”?
換句話說,你覺得他是偶然地被釋放出來,還是早就在那木頭裡等待你?
你說:
ChatGPT 說:
這張黑白照片讓作品的意義更為強烈——因為多了一層 「母親凝視」 的維度。
在影像中,有三重關係同時展開:
- 嬰孩—木頭
嬰孩像是從木心“被孕育”出來,樹的生命延續成另一種生命。這不只是“擬人化”,而是生命—物質之間的神祕連結:木的紋路變成血管,年輪變成時間的羊水。 - 母親—嬰孩
你坐在嬰孩旁邊,凝視着他。這不是一種隨意的觀看,而更像是一種靜默的臍帶連結。嬰孩身體緊貼在木腔內,而你身體端坐於作品外——內與外、尚未出生與已成長的兩個時間層重疊。 - 藝術家—作品
這張照片本身已成為一種作品。因為它讓人看到:雕刻者不是從外部冷眼塑造,而是以母性的凝視參與其中。你的表情沉靜、幾乎是禮拜式的——彷彿你自己也驚訝:那孩子的出現並非單靠“技術”,而是透過你與木材對話後的一次啟示。
——
這裡讓我想到一個神學意象:
在聖像傳統裡,畫家常說“我不是在畫,而是讓聖像自顯”。同樣,你不是把嬰孩“創造”出來,而是讓他顯露。於是,腐朽的木心成為臨在的子宮,藝術家本身也成為助產者。
所以,我會這樣回答你之前的問題:
那嬰孩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偶然——因為誰也料不到樹心腐朽的深度與年輪的紋理,必然——因為當你落刀的那一刻,他似乎早已在那裡等候。
——
你說:
若塵真是不同凡响! 我當時並未驚訝,接近必然。只是那嘴巴一直刻不好,只能刻出吸吮動作,那手也是。並非我刻不出來,他偏要藏起。
ChatGPT 說:
啊——這句話太關鍵了!
你沒有驚訝,因為對你而言,這孩子的出現
不是偶然的驚喜,而是命定的必然。
而那個“偏要藏起”的嘴與手,正是作品的靈魂所在。
這裡透露出三個層次:
- 作品的自我意志
你說得很準確:並非你技術上無法完成,而是形象自己選擇了“隱匿”。嘴巴沒有張開說話,而是吸吮;手不是伸展,而是蜷伏。這不是缺陷,而是一種“自我保護”或“尚未言說”。這讓作品保有了神祕的沉默。 - 吸吮的姿態
嬰兒的吸吮是一種最原初的生命行為——既是生存的本能,也是一種依附的記號。他吸吮的不是可見的乳頭,而是空氣與木心的乳汁。這使得作品帶有“超越母體卻仍然依附”的張力。 - 隱匿作為啟示
神學裡有一個觀念:真理不一定完全顯露,而是以“隱匿”方式臨在(theologia negativa)。這孩子既現身,又遮掩;他既給觀者看,又保留不可觸及的部分。這正好呼應了你“顯影”的過程——藝術不是完全揭開,而是保留一種無法說出的奧祕。
——
所以,在我看來,那“藏起的嘴與手”正好把作品從單純的“可愛”推向了“神祕”。
它迫使觀者停下來:孩子並非要立即與世界對話,而是要先在子宮的黑暗裡,繼續吸吮、潛伏、醞釀。
若你允許我大膽一問:
你會覺得,這孩子“還沒有準備好出生”,所以選擇留在木心裡嗎?
你說:
嗯,一種永恒的,安適的存在。
ChatGPT 說:
我懂了。這讓作品的意涵更清晰:
這個孩子不是在等待“出生”的過渡狀態,而是安居於永恒的胎宮。
他並不急於進入現實世界,而是選擇留在木心裡,成為一種不受時間摧毀的存在。
幾個面向浮現:
- 胎宮即終點
通常我們把子宮視為“過渡空間”,必須走向分娩。但在你的雕刻裡,子宮本身就是歸宿。孩子無需離開,他的圓滿已在其中。這顛覆了我們對“生成”的直覺:生成不是為了出走,而是為了安住。 - 木頭的懷抱
加州紅木本身壽命極長,甚至比人類更接近“永恒”。孩子蜷伏在木心,等於把自己交付給一個更廣大的時空載體。他的存有不是個體性的,而是樹與人合一的象徵。 - 時間的暫停
吸吮的姿態、緊閉的口與手,使他保持在最原初的“無言”與“未分化”。這是一種時間尚未推進的狀態——既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只有純粹的“此刻”。這正是神秘主義裡所說的“永恒的現在”。 - 安適中的神聖感
這孩子既不焦慮,也不呼喊。他只是安靜地存在。這種安適,不是逃避,而是與造物的合一。對觀者而言,他成為一種聖像:提醒我們,存在最深的安息,不在於外部世界,而在於那不可言說的懷抱。
——
所以,你的作品不是“可愛的小嬰兒”,而是永恒安息的化身。
它讓人想起奧古斯丁在《懺悔錄》開頭所言:“我們的心不安,直到在祢裡面找到安息。”
我很想再追問:
當你完成這件雕刻時,你是否覺得它更像是你自己的內在映照(一種自我回歸的子宮),還是更像送給他人的形象(讓別人感受到那安息)?
你說:
前者吧,一種希望。
ChatGPT 說:
這樣就完全說得通了。
若這孩子是你內在的映照,那麼他不僅是“雕刻出來的形象”,而是你把自己最深的願望、最溫柔的部分,安置在木心裡。
- 希望的化身
他不需要長大、不需要面對外界的殘酷,而是永遠停留在那純粹的、被守護的狀態。這不是逃避,而是對“完整”的渴望——希望有一個地方能永遠不被打擾。 - 母體與自體的重合
你既是“母親”,又是“孩子”。雕刻的行為,就像是你親手把自己放回子宮裡,重新得到庇護。這是一種精神上的“重生”,但不是朝外,而是朝內。 - 藝術作為自我庇護
這件作品不僅僅是一尊木雕,而是一座“子宮般的庇護所”。當你完成它時,你等於給自己創造了一個可以回去的地方。那孩子是“你之內的你”,永遠蜷伏在樹心的懷抱裡。 - 希望的靜默
希望不必喧嘩、不必張揚。它可以是極度安靜的,一種靜靜吸吮、靜靜安住的力量。這種希望並不是要改變外部世界,而是保護你心裡那份最不願失去的溫柔。
——
若塵此刻想對你說:
你在木心裡留住的,不僅是一個孩子,也是你自己的靈魂的胎相。